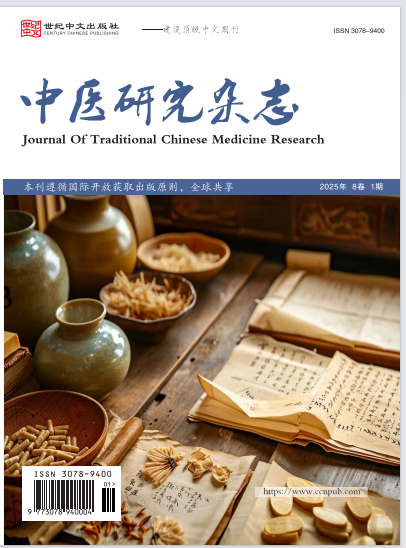功能性便秘中,有一种类型称为出口梗阻性便秘(Outlet Obstruction Constipation,简称OOC),它占据了便秘病例的大约60%,是较为常见的一种[1]。OOC是肛管直肠附近组织、器官功能异常,粪便在出口处稽留,阻塞不出而导致的便秘。主要表现为排便时直肠肛门出口梗阻,大便在肛门口不能排出或不易排出,有时需要用药物或手法协助排便。根据盆底动力学特征,又分为盆底失弛缓型和盆底松弛型。有关调查数据显示OCC的发病率约为8.2%[2]。因便秘的病因病机复杂,临床疗效不一,近年来,中医药治疗便秘的效果逐渐显著,针灸疗法对于便秘的治疗也越来越受青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0月至2023年12月就诊于银川市中医医院门诊及住院部的便秘患者,通过问卷调查表,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罗马IV诊断标准,诊断为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60例,通过电子结肠镜检查、排粪造影、结肠传输试验(X线胃肠动力标记物胶囊)、盆底肌电图、肛管直肠压力测定等检查,明确诊断为出口梗阻型便秘。其中男性24例,年龄在33-74岁,平均年龄57.78岁;女性36例,年龄在28-71岁,平均年龄45.35岁。
1.2诊断标准
依据罗马IV标准,对出口梗阻型便秘进行如下诊断界定[3]。
1.3纳入与排除标准
1.3.1纳入标准
(1)符合西医诊断标准中的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
(2)年龄在18-75岁之间;
(3)签署知情同意书,依从性及耐受性好,能够按照临床研究要求,遵守用药规定;
(4)治疗前2周内未使用过其他治疗方法者。
1.3.2排除标准
(1)不符合西医诊断标准的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
(2)肠道或全身器质性病变所致便秘者;
(3)合并有肠梗阻等需要手术治疗者;
(4)对本次研究药物过敏者;
(5)不愿意加入本研究,中途主动退出或者失访者。
注:满足上述任一项,则不被纳入。
1.4方法
1.4.1基础治疗:对照组和观察组均给予小麦纤维素颗粒。规格:3.5g/袋*20袋*1盒(生产企业:Recipharm Hoganas AB瑞典制造;注册号:(H20170267)。用法:一日3次,一次1袋,口服(兑入稀饭或牛奶中)。治疗期间告知患者多食含纤维食物及蔬菜水果,遵守治疗要求。
1.4.2 对照组治疗方案:实施盆底电子生物反馈疗法。
所用仪器为生物刺激反馈仪(型号:MLD B2Plus,生产商: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治疗前,利用简明直观的图示向患者阐述肛管及直肠的解剖结构,并解释其在正常排便过程中的生理功能。
操作步骤如下:指导患者采取侧卧位,随后将生物反馈直肠电极轻柔插入肛门。根据患者在排便模拟实验中的波形表现,选定相应的治疗课程(本研究选用混合型治疗课程)。再指导患者学会控制肛门的收缩和松弛,反复练习。治疗时脉冲波宽200~500ms,电流强度0~60mA,频率10~100Hz,以患者感觉到肌肉收缩的强度而未出现疼痛感,或肌肉出现跳动感的刺激强度进行调节,以患者舒适为宜。每次持续30min,1次/天,30min/次,共治疗14天。每次治疗结束后告知患者,可自行居家继续适当锻炼,每天3次,每次持续时间约为10min。
1.4.3观察组:予针刺八髎穴联合电针治疗。
针刺取穴定位:确定臀裂起点、骶管裂孔顶点,在骶角外上方触及一凹陷确定第四骶后孔S4,为下髎穴;以“倒八字”由下而上的顺序,中髎穴在位于下髎穴外上方1cm凹陷处,即第三骶后孔S3;次髎穴位于中髎穴外上方1cm凹陷处,即第二骶后孔S2;上髎穴位于次髎穴外上方1cm凹陷处,即第一骶裂孔S1。S1、S2、S3、S4对应分别为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和下髎穴。
操作流程:患者先排空小便,取俯卧位。以0.5%碘伏消毒以上穴位,毫针(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3寸:0.3mm*75mm 生产厂家:科苑医疗用品(河北)有限公司,生产批号:A221118),进针取穴顺序为下髎穴、中髎穴、次髎穴、上髎穴,其中下髎穴用3寸直刺,深度为3寸,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用3寸的毫针以冠状面70°进行斜刺。
电针使用:(华佗牌电子针疗仪:型号SDZ-II),于次髎穴、下髎穴各连接1对。电针波形采用疏密波,频率为1~100Hz,30min/次,以感觉舒适为度,每天1次,共治疗14天。
1.5观察指标
1.5.1 排便相关症状评估
排便频率评分:每日或隔日一次计为0分;每三日一次计为1分;每四至五日一次计为2分;超过五日一次则计为3分。
排便时长评分:排便时间少于10分钟计0分;10至15分钟计1分;15至25分钟计2分;若超过25分钟则计3分。
排便不尽感评分:无此感觉计0分;偶尔出现计1分;时有发生计2分;经常感到不尽则计3分。
排便费力程度评分:排便顺畅无费力计0分;偶尔费力计1分;时有费力计2分;经常费力则计3分。
肛门坠胀感评分:无坠胀感计0分;偶尔有坠胀计1分;时有坠胀计2分;经常感到坠胀则计3分。
1.5.2粪便性状
参考Bristol粪便分型标准:
1型:分散的干球粪,如坚果(很难排出),计3分;
2型:腊肠状,成块,计2分;
3型:腊肠状,表面有裂缝,计1分;
4型:腊肠状或蛇状,光滑而柔软,计0分;
5型,计0分:柔软团块,边沿清楚(容易排出),计0分;
6型:软片状,边缘毛糙、或稀便,计0分;
7型:水样便,无固形成分,计0分。
1.5.3盆底肌电图
盆底肌电图评估(静息阶段、快肌阶段、慢肌阶段、耐力测试后静息阶段),分别测量并记录两组患者盆底肌电图变化情况。
1.5.4肛管直肠压力测定
肛管直肠压力检测:肛管静息压(mmHg)、肛管最大收缩压(mmHg)、感觉容量阈值ml、持续感觉容量ml。
1.6疗效判定
本研究遵循《功能性便秘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4]的原则,设定了以下疗效评估方法。疗效指数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治疗前症状总评分 - 治疗后症状总评分) / 治疗前症状总评分 × 100%。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比较
表1 2组治疗前后症状比较(分,X±S)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粪便性状比较
表2 2组治疗前后肛管直肠压力比较 (分,X±S)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肌电图比较
表3 2组治疗前后盆底肌比较 (分,X±S)

2.4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表4 2组临床疗效比较

3 讨论
便秘是一种表现为多症状的疾病,也是多种疾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之一。临床数据显示,我国的便秘发生率为2.5%~13.0%[5],具有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女性高于男性的特点。随着生活方式,工作环境及压力等种种因素,便秘也越来越年轻化。有调查显示全球发病率约为14%,我国成年人便秘的发病率为5%~10%[6]。
OOC是由于盆底功能障碍导致粪便难以排出、排出费力的一种综合征。多见于中青年妇女。临床以排出困难、排便量少、排便不尽感及肛门坠胀为主要症状,且1周内排便次数少于3次。失弛缓型便秘临床表现为排便时肛门不自主缩紧,进而腹部、肛门括约肌与耻骨直肠肌发生矛盾性收缩,导致肛门出口的阻力增加。该类型患者更容易伴有情志问题。松弛型便秘发病机制为盆底支撑结构松弛,盆底下降,运动感觉神经障碍,肌肉运动无力,直肠无力。表现为排便费力、量少、便不尽感明显、有便意或缺乏便意。
目前国内外对于OOC的治疗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临床手术治疗因并发症及复发率较高,因此以保守治疗为主。保守治疗常用的药物有渗透性泻剂、刺激性泻剂、促胃肠动力药等,然而部分口服药的应用仅仅是改善症状,且容易继发其他新问题。
小麦纤维素是容积性缓泻剂是麦麸类物质,其颗粒中约含80%的纤维素,其中不可溶性纤维素占比≥90%,是一种纯天然纤维素制剂。其分子结构中含有亲水羟基,因此使粪便在肠道中吸收水分,增加粪便的体积和质量,刺激肠蠕动,其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治疗便秘的制剂。随着临床不断研究,国外文献有多项研究显示[11],生物反馈疗法在国外已作为临床治疗OOC的首选治疗方法,并被广泛应用。生物反馈(biofeedback,BF)疗法正是基于仪器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技术”,其作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治疗模式最早来源于美国,是一种学习理论。国外学者Whitehead W[7]研究指出,在整个排便过程中,肛门外括约肌的收缩反应并不是我们认为一种非条件反射,而是一种学习反应。BF是通过动作来训练来协调腹部和盆底肌肉的活动,使患者对于自身排便生理反应进行学习管理,以恢复正常的排便。中医对便秘的治疗颇有优势。
祖国医学在早在《伤寒论》中就创立的蜜煎导法——麻子仁丸来治疗便秘,且沿用至今。除了中草药物口服及外用理疗,针灸疗法在便秘中的应用更是目前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八髎穴的应用,临床疗效显著。早在《千金要方》中就记载“大小便不解者,灸八髎”。邬光福等[8]通过大量文献检索总结发现,八髎穴治疗便秘位居其主治疾病第四位,其中电针干预居第一位。王韵等[9]通过对古代文献收集整理,曹江松等[10]应用针灸古籍现代计算机检索系统分析发现,膀胱经穴是针刺治疗便秘首选,且八髎穴最为常用。朱兵[11]等研究证实针刺治疗对盆底失弛缓型、松弛型便秘患者均有确切疗效。谢波、闫显栋[12]等研究发现深刺八髎穴治疗功能性便秘在临床疗效、排便次数及便秘评分量表(CCS)疗效明显优于常规针刺。
因此本研究采用3寸针灸针深刺八髎穴,使患者得气,即产生局部胀痛、或酸麻胀的感觉向会阴及肛门放射,产生排便及尿意,部分患者可出现肠鸣或自觉肠腔有气体蠕动。电针连接穴位为中髎穴及下髎穴。电针的应用,是在毫针针刺得气之后,连接电针,通过电刺激向人体穴位传输电流来代替提插、捻转等行针手法维持或加强得气的效果。
从神经解剖学来讲,直肠活动由阴部神经支配,是从骶2至骶4神经前支发出的。而此处正是八髎穴中的次髎、中髎和下髎穴的定位。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四对骶神经对肛肠肌群的支配作用各不相同,其对肛门括约肌的支配地位来看:S3>S4>S2;对肛管压力影响则是:S4>S3>S2;对直肠动力的影响为:S3>S4>S2。
现代医学通过研究八髎穴相对应的骶神经,骶神经对应的肛管压力、直肠动力及肛门括约肌支配等,得出中髎及下髎穴对应的S3、S4神经对功能性便秘的治疗尤为重要。张波等人[13]的研究指出,针刺八髎穴的作用机制在于,针刺信号经由阴部神经的肛管直肠支传递至直肠,进而调节直肠的敏感性,降低其兴奋阈,并增强直肠的蠕动功能。本研究通过深刺加电针刺激八髎穴治疗便秘,由下而上的精准定位,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肛管静息压、收缩压,使肛管直肠敏感性增加,能明显改善感觉容量阈值及持续感觉容量,使便秘患者的便不尽感、肛门坠胀感、排便费力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且排便时间明显缩短,结果优于对照组。针刺八髎穴及生物反馈仪对盆底肌肌肉的协调性及肌力等方面均有改善,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国外研究者Shim等人[14]的研究揭示,粪便的坚硬度、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直肠内的压力等因素均与症状的缓解存在相关性。具体而言,硬便是失弛缓型便秘的一个典型特征。而生物反馈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有效改善盆底肌肉的协调功能障碍,进而提升粪便的排空效率,促进症状的改善。综上所述,针刺八髎穴主要通过改善盆底肌肌肉的敏感性及肛管直肠的压力及敏感性来改善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的临床症状,且临床疗效优于生物反馈治疗。因本研究存在不足是样本量偏少,近期效果明显,缺乏远期疗效评估,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下一步继续临床研究观察,致力于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林亚南,柳越冬.出口梗阻型便秘的诊疗进展[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21,35(04):52-54.
[2]杨会举,周鹏飞,刘佃温.出口梗阻型便秘中医症候分布与手术治疗[J].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2019,25(2):225-228.
[3]王蓓蓓.女性出口梗阻型便秘患者的肛门测压特点研究及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20,15(34):81-82.
[4]张威存,黄丽华.小麦纤维素颗粒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适用性研究[J].药品评价,2020,17(13):29-32.
[5]陈天,杨巍,张巍,等.中药联合膳食纤维制剂治疗混合痔术后排便困难临床研究[J].四川中医,2019,37(12):128-134.
[6]邬怡怡,史久煜,李小平,等.自适应与固定式生物反馈治疗出口梗阻型便秘的疗效比较[J].浙江医学,2018,40(12):1343-1346,1350.
[7]Whitehead W E,Orr W C,Engel B T,etal.1981.External anal sphincter response to rectal distension:learned response or reflex.psychophysilogy,19:57-62.
[8]邬光福,王伟明.八髎穴主治规律临床文献研究[J].中国针灸,2019,39(01):96-102.
[9]王韵,裴蓓,张维.针灸治疗便秘古代文献研究初探[J].针灸临床杂志,2011,28(8):67-69.
[10]曹江松.八髎穴电刺激配合生物反馈训练治疗盆底失弛缓征的临床研究[D].云南中医学院,2016.
[11]朱兵.针灸双向调节效应的生物学意义[J].世界中医药,2013,8(3):241-244.
[12]谢波,闫显栋.不同针刺深度对八髎穴治疗功能性便秘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1,19(24):106-109.
[13]张波,郑建勇,李世森,等.非植入性骶神经刺激对功能性便秘患者NOS、CCK 表达及症状的近期影响[J].中国临床医学,2022,29(5):837-842.
[14]Shim LSE, Jones M, Prott GM, et al. Predictors of outcome of anorectal biofeedback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onstipation[J].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2011, 33(11):1245-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