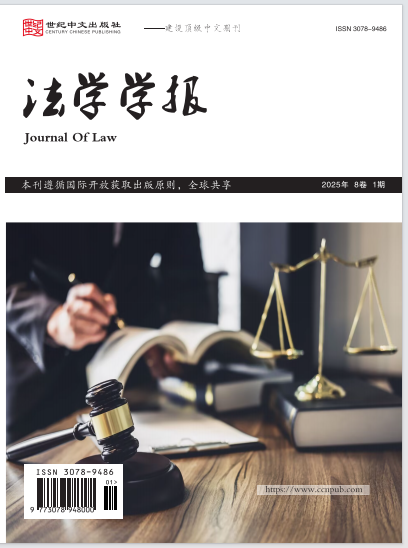在英国近代化转型中,圈地运动打破了传统敞田制,最早确立了个人土地私有产权,因此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一般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15、16世纪的都铎圈地,17世纪的圈地和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第三阶段,对17世纪的圈地关注相对不足。17世纪往往被视为英国两次大规模圈地之间的间歇期,1然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托马斯·爱德华·斯克鲁顿和拉塞尔·M·加尼尔发现,17世纪英国存在大面积的沼泽排水圈地和森林圈地。2沃迪在其英国圈地年表中提出,17世纪是英国圈地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时期。3除圈地规模外,伦纳德和冈纳先后论证了英国圈地运动的连续性。伦纳德分析了17世纪英国米德兰地区圈地暴动频繁而圈地率低的矛盾现象,介绍了此时的圈地模式和程序。4冈纳延续伦纳德的研究,提出17世纪英国圈地中协议逐渐取代无序,其圈地模式既有对早期圈地的继承,又为下一世纪做了准备。5耶林从长时段考察认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后期英国盛行的协议圈地,是向议会圈地的过渡模式。6
上述研究已经就17世纪英国圈地问题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即圈地运动在17世纪未曾中断,反而愈发频繁。17世纪圈地以协议圈地为主要形式,其圈地程序和模式为议会圈地提供了借鉴。然而,前人研究主要聚焦于17世纪英国圈地的规模和表现,未能就协议圈地盛行的原因及其特点予以充分说明。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英国大法官法庭圈地诉讼法令手稿,拟从法律视角分析17世纪英国协议圈地盛行的原因、17世纪协议圈地的程序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学界圈地研究有所补充。
一、虚假诉讼协议圈地的背景
英国圈地运动起始于中世纪,本质上是土地产权的再分配与确认活动。在传统敞田制下,农民持有的条田散落在庄园各处,且必须由村庄共同体统一安排耕作,土地的分散和使用限制给农民的生产管理造成诸多不便。而庄园领主也不满于价格革命下土地的固定低额地租。因此,以“近代私有产权下不受限制的土地使用形式”取代敞田制的圈地,7成为领主和农民的共同需求。然而,自都铎王朝至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政府,并未就圈地予以认可,反而将人口减少和谷物歉收等问题简单地归因于此,数次颁布禁止圈地的法令。
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延续了都铎王朝的禁止圈地政策。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就颁布了一项《延续、恢复或废止若干法规》的法令,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禁止圈地政策加以继承,其中包括1597年的《禁止破坏城镇和农舍法令》和《保护耕地法令》。8第一项法令针对有关圈地导致的农舍破坏及流民问题,法令规定:禁止破坏农舍和城镇,废除迄今为止与此相悖的法规;被毁农舍已超过7年的,半数以上由毁坏违法者重建,每座农舍附带40英亩土地;最近7年内被损毁的农舍,由违法者全部予以重建,每座农舍附带20或40英亩土地(视原有土地数量而定);法令允许领主与佃户或在领主同意下佃户与其他人置换土地;未重建农舍的违法者每年每座农舍罚款10镑,未附带土地的违法者每年每英亩罚款10先令;罚款分为三等份,分别交给女王、教会和检举人。9从该法令可以明确看出,17世纪初的斯图亚特王朝反对圈地,对于侵占农舍和土地的圈地行为予以惩处,并鼓励检举揭发。从17世纪初期斯图亚特王朝的政策来看,至少在政府大多数人看来,圈地是导致农村人口减少、粮食减产和流民等问题的直接诱因,因此必须颁布禁止圈地的法令,不仅对破坏土地和农舍的行为予以制止,甚至还要将其恢复原状。此后,针对地方反圈地暴动和粮食减产等问题,政府多次组织圈地调查。在1630年11月,枢密院为应对粮食短缺问题开展圈地调查,给德比郡、亨廷顿郡等五个郡的治安法官去信,要求他们调查两年内的圈地和土地转变情况,信中认为:“耕地转变成牧场对民众造成了损害,圈地和耕地转变一直在造成人口减少,这违反了王国法律传统,造成负面结果。尤其是在此国家粮食短缺之时,如果不能及时制止,民众普遍担忧此类耕地转变愈演愈烈,最终可能会危及公共利益。” 10因此,面对不同时期的地方暴动和粮食减产等问题,政府将其简单地归咎于圈地,反复调查并予以制止。
在17世纪政府反圈地的法律背景下,何以圈地面积还能持续扩大,圈地者如何实现圈地需求?那就是,以大法官法庭虚假诉讼的方式推行协议圈地。圈地者互相串通起来,以产权纠纷为由向大法官法庭提出诉讼,法庭在审理诉讼的同时,对圈地者所提交的圈地协议进行确认,并为此颁布裁决法令,从而使该圈地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
协议圈地引入法庭诉讼,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法庭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圈地协议获取法令记录,以确认圈地事实。例如,在1629年大法官法庭审理的北安普顿郡金斯索普区(Kingsthorp)一场协议圈地诉讼中,被告牧师克拉克(Clark)的部分圣职躬耕田位于原告摩根(Morgan)的圈地范围内,双方已提前就该问题达成协议。原告为了使圈地获得法令认可,以教会财产继承存在限制为由,要求法庭派遣委员会调查圈地情况。最终,大法官法庭颁布法令确认,原告及其继承人和受让人享有上述圣职躬耕田的自由使用权,被告及其继任者享有上述圈地协议规定补偿的自由持有土地。11法庭确认正是增强双方协议效力的一种方式,不仅确保当事人同意协议,而且对其继承人也形成约束,更是通过法庭颁布的法令确认了圈地的既成事实。
其二,圈地者通过引入诉讼程序胁迫反对者,排除圈地干扰。事实上,“提出圈地倡议的产权人很难靠一己之力推进圈地,除非圈地教区只有一个产权人”。121664年5月11日,大法官法庭审理蒂尔维顿(Thirveton)起诉科利尔(Collier)的公地协议圈地案中,根据协议,公地被分配为18块份地,然而却只有15人出席诉讼。被告对此提出反对,认为签订协议和出席诉讼的不是同一批人,此外还存在一些宣称在公地上保有公共权利的其他人,他们既未参与协议,也未参加诉讼。在此情况下,为该协议颁布法令,将会是明显的错误,并会引起新的诉讼纠纷。然而,法庭最终还是为该协议颁布了确认法令,“上述圈地协议应予执行,任命委员会核查每个人的所有权。如有任何存在利益关联但未参与协议的人,他们不受此约束,如此便没有损害。但是,这不应作为个别顽固者妨碍公共利益的依据”。13在部分产权人未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法庭通过了圈地法令。此类法令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对反对圈地者形成法律压迫。
二、虚假诉讼协议圈地的程序
以虚假诉讼的形式进行协议圈地,其实施程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协议的拟定、圈地的实施和法庭诉讼。拟定协议是圈地者确定产权人土地持有权和公共权利并确立圈地基本原则的阶段。圈地的实施由圈地委员会根据圈地协议全权负责。法庭诉讼则是协议圈地的确认阶段和核心程序,往往采取虚假诉讼的形式。三项程序并非总是依序进行的,法庭诉讼可在圈地完成若干年后再提出,也可能与圈地同时进行。
圈地协议的拟定是圈地者根据全部同意原则协商、裁定的结果。首先,圈地倡议人需召集各方利益代表参与协商会议。倡议人一般是当地的土地产权人,其身份并无限定,庄园领主、教区牧师、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等均可发起圈地。其次,由产权人代表任命一个圈地委员会负责本次圈地事宜,委员会人数不一,一般是四个人,其中两名委员代表村庄共同体利益,另外两名分别代表庄园领主和教区牧师的利益,14有时也会任命土地测量员。圈地委员会的任命考虑到各方利益,以免圈地过程中对其中一方有所损害。最后,圈地委员或测量员对土地进行调查勘测,确认每个产权人持有的土地和公共权利,并据此拟定圈地协议和圈地裁定书。在此过程中,敞田制下复杂的土地权利得到再分配。产权人所持有的分散的可耕地,以及基于此占有的草地、可放牧牲畜的数量和泥炭权、木材权等公共权利,皆由一块所有权完整的份地替代补偿。该圈地协议需获得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自愿同意。圈地协议获取所有产权人的同意是其提交至法庭诉讼的必要前提。圈地协议和裁定书经所有产权人同意后,由圈地委员会照此实施圈地。圈地委员一般是受圈地者委托,代表其利益的当地人,全权负责圈地具体事宜。
法庭诉讼是17世纪协议圈地的核心程序。如前所述,这一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借法庭权威保证圈地过程和结果的稳定,然而本是非法行为的圈地如何才能介入到法律程序?于是虚假诉讼就产生了,圈地者以协议存在产权纠纷为由向大法官法庭提出诉讼,“存在纠纷是一个必要的假设,否则法庭的权力无从介入”15。 1655年牛津郡黑丁顿区(Heddington)马斯顿教区(Marston)的圈地就是一次典型的虚假诉讼协议圈地。内战期间,该教区土地因牛津市驻军破坏而荒废,战后当地居民协商通过圈地改良土地,1655年所有产权人和利益相关人签字确认同意圈地协议,并委任绅士约翰·怀廷(John Whiting)为测量员负责土地的勘测和分配。期间,乡绅布鲁姆·沃尔伍德(Broom Whorwood)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圈地协议。然而,圈地完成数年之后的1661年,以乡绅维顿·克鲁克(Vnton Croke)为代表的自由持有农们向大法官法庭起诉布鲁姆·沃尔伍德,他们宣称圈地带来了财产增长,被告也从中受益,但是他却以圈地会导致什一税减少为由,威胁推翻圈地,重新恢复敞田。原告认为被告干扰了他们的土地保有权,要求大法官法庭对1655年的圈地协议进行确认。沃尔伍德对此回应,他承认原告所说的马斯顿教区的圈地,也承认他对圈地协议的同意,圈地是有利于原告和公共财富的,圈地协议应该得到大法官法庭的确认。最后,大法官法庭裁定,该协议圈地经原告陈述和被告承认,现颁布法令予以确认,原告及其继承人和受让人可永久自由保有上述协议圈地。16该案中,圈地协议已签订6年之久,被告布鲁姆已从圈地中受益,也承认圈地对财产增长的进步意义,其反对圈地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被告对原告的陈述完全予以承认,当事双方并未就诉讼纠纷产生任何争执,反而一致要求大法官法庭对圈地协议予以确认。冈纳认为,这种虚假诉讼过程就是当事人的一出表演,其目的仅仅是法庭对圈地协议的确认。17经过大法官法庭对虚假诉讼的审理,圈地协议取得法庭审判的确认,进而使圈地这一事实获得法令权威的保护。
在17世纪英国法庭诉讼协议圈地程序中,圈地者在圈地协议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引入了虚假诉讼,使圈地协议获得大法官法庭的法令确认,从而赋予圈地既成事实以一定的法律权威。在政府禁止圈地的法律背景下,虚假诉讼协议圈地为17世纪英国的土地确权提供了一种追求法律效力的途径。然而,虚假诉讼是圈地者为获取法律确权的无奈之举,究其原因是此时的圈地程序缺乏必要的法律认可和制度设置。
三、虚假诉讼协议圈地的不足
在17世纪英国政府禁止圈地的法律背景下,基于土地确权需求的领主、乡绅、大农和自由持有农等土地产权人,为了使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圈地具备法律约束力,创造性地引入法庭诉讼程序确认圈地,以保证对圈地过程的推进和圈地结果的维护。然而,法庭诉讼协议圈地的程序限制和漏洞,却也注定其终将被淘汰的命运。
第一,圈地协议需全部产权人自愿同意。大法官法庭对圈地协议确认的前提是,相关土地所有人完全且自愿同意裁定协议,且圈地不能造成任何减少人口、破坏农舍和妨碍公路交通的问题。18然而,获取所有产权人同意并非易事。尤其是没有或只有小块土地的茅舍农和小农,他们认为圈地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公地传统习惯所赋予他们的放牧权、木材权、泥炭权等公共权利是其贫穷生活的重要补充,而圈地的目的恰恰就是取消这种复杂的公共权利。乡村雇工也认为圈地必然导致他们的就业率下降,进而降低其生活水平。19因此,圈地倡议人不得不反复游说土地产权人,甚至对其做出必要的妥协。1594年沃里克郡弗兰克顿(Franckton)圈地中,圈地者约翰·坦普尔(John Temple)无偿给予当地牧师托马斯·利森(Thomas Leeson)20镑才获取他同意圈地。20全部同意原则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小农利益,但对急于达成圈地协议的领主或大农等倡议人而言却是一种阻碍。面对个别顽固的反圈地者,他们以长期且昂贵的法庭诉讼相威胁,迫使其同意圈地。如此,全部同意原则并未能完全避免对小农的损害,反而使圈地程序更加复杂化。
第二,法庭诉讼程序的引入需以存在产权纠纷为前提。圈地者自发组织的协议圈地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为此不得不向大法官法庭诉求法律权威。然而,大法官法庭确认圈地协议的前提是,圈地者之间存在产权纠纷并以此为由向法庭提出诉讼要求。因此,为了使圈地具备法律效力,圈地者往往串通起来伪造产权纠纷,就协议条款和圈地事实等问题达成共识,21仅以不承认协议等无关轻重的理由提起虚假诉讼。在政府禁止圈地的法律背景下,协议圈地缺乏获取法律确认的程序设置,造就了虚假诉讼这一追求合法的违法行为。
第三,法庭权威的不稳定性。大法官法庭因其权威性而成为圈地者诉求法律效力的选择,然而在国王法令禁行圈地的情况下,法庭所赋予的这种权威是否一直可靠呢?答案是否定的。1666年10月30日,一份“确认衡平法院22法令圈地的法案”被提交至议会上议院,该议案经过二读后交由一个委员会继续讨论,但是讨论会议一直被推延,直到该届议会结束,议案也未获通过。23冈纳认为:“如果该法案被通过的话,圈地最活跃的时期可能会因此提前将近一个世纪出现,而且也不一定会再诉求于私人法案圈地。”24议会对大法官法庭所颁布的圈地法令的否定,表明至少在圈地一事上,议会的权威已在大法官法庭之上。大法官法庭不能赋予圈地稳定的法律权威,使圈地者不得不诉诸于更具权威的议会法案,而圈地诉求对象的转移也体现了17世纪英国政权的变动。
结语
17世纪英国的协议圈地,本质上仍是近代土地产权人追求土地确权的活动。然而,政府囿于人口减少和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未能就圈地问题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和规范。土地产权人为此不得不通过大法官法庭的虚假诉讼形式,为圈地附加一定的法律权威。17世纪以法庭诉讼方式赋予协议圈地以一定合法性,是英国圈地历史上的一次创新。然而,在17世纪国家法令禁止圈地的法律背景下,圈地协议获得所有土地产权人的一致同意,是其进入法庭程序的必要前提。这一原则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贫困小农的权利,但毕竟作用有限,而且妨碍了土地确权的推进。此外,法庭诉讼的引入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设置,以至于大量的圈地诉讼都是非法的虚假诉讼。随着17世纪末议会最高权威的逐渐确立,土地产权人发现大法官法庭并不能给予圈地事实稳妥的保障,转而越来越多地诉求议会法案进行圈地。
1. W. J. 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art II,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8, p. 286; Edwin F. Gay, “The Inclosure Movement in England”,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6, No. 2(May, 1905), pp. 146-159.
2. Thomas Edward Scrutton, Common and Common Fields,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7; Russell M. Garnier,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ded Interest: Its Customs Laws and Agriculture,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1892.
3. J. R. Wordie, “The Chronology of English Enclosure, 1500-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6, No. 4, Nov. 1983, pp. 483-505.
4. E. M. Leonard, “The I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9, 1905, pp. 101-146.
5.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6. J. A. Yelling, Common Field and Enclosure in England 1450-1850,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7.
7.Harriett Bradley, The Enclosure in England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1918, p. 9.
8. The Statues of the Realm, Vol. 4(1547-1624), p. 1050.
9. The Statues of the Realm, Vol. 4(1547-1624), pp. 891-893.
10.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Vol. 46(1630-1631), p. 138.
11. The English Reports, Volume XXI, London: William Green & Sons, Edinburgh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02, pp. 501-502.
12. 倪正春:“英国议会圈地的实施程序及其特点”,《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3期。
13. The English Reports, Volume XXII, London: William Green & Sons, Edinburgh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02, p. 688.
14.W. E. Tate, 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and the Enclosure Movement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67, p. 47.
15. Maurice Beresford, “Habitation versus Improvement: The Debate on Enclosure by Agreement”, in F. J. Fisher,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58.
16.Chancery Enrolled Decrees, February 12, 1662, Roll 586, no. 1,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London.
17.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p. 55.
18. P. A. Penfold (ed.),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Volume 46, 1630-1631,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4, p. 349.
19.W. H. Hosford, “An Eye-Witness’s Account of a Seventeenth-Century Enclosur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 No. 2, 1951, pp. 215-216.
20.Chancery Enrolled Decrees, January 31, 1612, Roll 194, no. 4,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London.
21. 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p. 55.
22.即大法官法庭。
23.Journal of the House of Lords, Vol. XII, p. 20, p. 28, p. 40, p. 66.
24. 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2, p.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