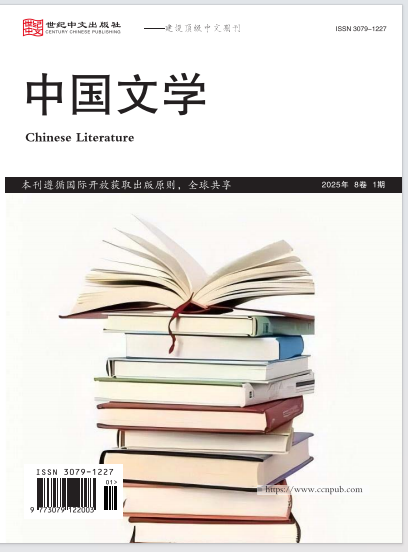“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自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后,在世界各国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同其他文论一样,这两个概念的成熟与繁荣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学者的态度也经历了一定的转变。自瞿秋白第一次将这两个概念引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就已经在中国有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相关学者更注重于“莎士比亚化”于现实主义的比喻意义。而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便似乎更注重其生动丰富性。而对于“席勒式”的理解,人们则多从“莎士比亚化”的反面来理解。但现今,随着政治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变化,人们逐渐对“席勒式”的客观理解与阐释产生了新的思考。
一、概念追溯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马克思1859年4月19日在伦敦《致斐迪南•拉萨尔》一信中。这封信是应拉萨尔的要求,马克思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一剧本是斐迪南·拉萨尔为反对通过自下而上的激进革命道路来统一德国而作。拉萨尔以十六世纪的骑士起义的失败,比附1848—1849年间革命失败,他认为都是"智力过失"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他认为,济金根是因为自己“有限手段”中的“狡智”而尝败果。但实际上,结合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显然是济金根自己身处的骑士阶层导致了这样的悲剧。骑士阶层作为封建阶层的武装力量,自身是封建阶层的帮凶,所以才会因为缺少群众基础而失败身死。而马克思所批评的拉萨尔违背历史逻辑确定的"主题",并且简单地以为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这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幻想的结果。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展现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基于现实角度的思考。而这封信在后世也被认为是马克思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学观点,这一组概念强调:文学作品应当“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能“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
二、“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概念发展
“莎士比亚化”的要义在于基于生活,表现生活,体现人物作为人的复杂性,更再现生活的复杂性。而席勒式便是指过于概念与理想的人物及强烈的时代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不能“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文学的思想与倾向性应当从作品的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莎士比亚戏剧的伟大和杰出之处在于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内在丰富性,更再现了生活的复杂;其人文主义倾向性也体现在他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和把握、对历史状况的真实感受和认识融会在一起。陈众议所长曾从“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切入评议马克思文艺观,谈情节与主题的关系。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如此经典,是因为在情节由高到低与主题由低到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恰好于莎士比亚时代达到最完美的交叉,以此谓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李旭中副校长也曾对“莎士比亚化”进行全面阐释,分别从性格刻划、内心世界洞察与真实细节阐释“莎士比亚化”的意涵,并且例举莎士比亚的诸多作品,从情节、情感与细节论其艺术张力,以及从开掘生活源泉、反映人民创造和直指人心情感等角度来谈“莎士比亚化”对于繁荣发展我国戏剧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与相关启示,即对于现当代较为浮躁的文坛的发展,用朴素形式来表现现代的思想或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莎士比亚化”在中国的发展与相关研究只是这一理论对于文学的冰山一角。受各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相较于国内,“莎士比亚化”在国外的发展似乎更为明显与强烈。19世纪“莎士比亚化”在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发展中影响十分广泛,为各国浪漫主义所取。以典型的法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化”在法国的发展基于当时法国古典主义的日益僵化与外国文学的吸引与冲击,在理论先驱的引导下,一步步由有志之士确立、发展直至兴盛起来。夏多多副教授与许莲花副教授曾具体阐述了“莎士比亚化”在西方的演进过程中尤其是法国浪漫主义者确立了范式,通过研究其发生发展的逐步深入的过程,来追溯“莎士比亚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先驱者斯塔尔夫人、坚定的捍卫者司汤达以及真正确立这一范式的领袖雨果,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相关成就。“席勒式”作为对立于“莎士比亚化”的文学概念,存在过于抽象、脱离现实,成为传声筒的弊端。而人们也常常会直接地把“席勒式”作为概括席勒本人创作的全部来进行批评。然,在笔者认为,“席勒式”其实并不是马克思对于席勒本人剧作的批判,而是对于唯心主义创作倾向的批判。而对于“席勒式”的学术研究也似乎一直都缺乏大家气派,人们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将“席勒式”抛之脑后而不做细究,我们当客观地审视“席勒式”,客观地进行探索。但笔者认为,“席勒式”依然有其进步意义,他为审美理想与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现实中所存在的人性的感性与理性都会成为不可避免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席勒或许就是因为未能处理好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因此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光芒副教授曾指出,诚然席勒的美学思想与其创作实践存在矛盾,但这其中恰恰是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间的矛盾最有价值。席勒的问题在于“理性的人”与“审美的人”相矛盾,常有学者提及此处便是直接定论席勒陷入“自我循环”,但这两个绝对价值间之所以难以平衡的根本是他自身的切合实际的思考。而席勒所提出的这审美与理性这两者中间“调和状态”与新的动态的“第三种状态”的概念区别正是席勒式的张力所在。
三、“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实践运用
“莎士比亚化”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虽然往往外部的政治环境与文学创作趋势并没有那么自由,但它依然对于国内创作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成就了一批作家。曹禺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齐名,无疑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而曹禺最为独特的一点便是他对于“莎士比亚化”的中国式创新,虽然处在“席勒式”的创作时代,但他兼收并蓄,吸收西方戏剧创作特点并结合东方特色而使他在30年代的剧坛上独放异彩。其作品中的情节结构吸收西方近代戏剧闭锁结构来构造冲突,加以主副线交织,以表现中国式的审美风格。此外,恩格斯1859年5月24日致拉斐尔的信中提到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的“三融合”的美学原则在曹禺剧作中以人物与环境交织加上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与浓厚的戏剧氛围展现出来。而对于人物的形象刻画,曹禺首先是塑造使人爱恨交织,集肯否于一身的悖论性格。其次,曹禺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用阶级性取代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是将两者融合,展现出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了人物性格与情感的简单化、平面化。然后,他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兼有鲜明复杂与独特之处在于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用现代主义方式来表现。最后,张芳彦曾细致地论述了曹禺在情节生动性与人物形象刻画的复杂性丰富性的结合上形成独特的艺术成就,并提出,曹禺对于人物刻画与性格塑造,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物心理与思想感情。显然,曹禺带领中国戏剧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美学特征便是以西方近代戏剧创作方式与技巧创造出具有中国传统审美特征的现代话剧。那么与曹禺话剧创作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当下电视剧作的快餐式倾向以及它带来的泡沫四溅的空虚感。瓦尔特·本雅明提出,文化渐渐从对传统的崇拜价值转变为展示价值,感知艺术作品的方式也渐渐以消遣式代替了凝神专注式,外在美成为大众需求。但这并不是电视剧逐步走向快餐式的理由,而更应该是一种对于电视剧未来发展的良好的引导与指向。我们应当有所追求,而不是一味服从于消费市场,甚至毫无底线。郄程副部长提出,电视剧作品在现代特殊需求与消费视域下,一方面要坚守思想立场,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莎士比亚化”地传递主流意识形态而为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当注重受众心理,以激情思辨为目的,通过感性的方法表达共同的情感,围绕典型塑造挖掘新元素,使语言雅俗共赏。当然,随着大众审美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受众对于电视剧作品的质量与其审美与娱乐性的兼顾提出要求。因此,也有部分优秀的作品随之呈现在大众视野。例如张翼肯定了《大明宫词》以富有时代内蕴与诗意,结合思辨的创作个性而带有莎意。整部剧是以诗为目的的戏剧路数,加上诗化的激情对白,而带有“莎士比亚化”的文化正餐的味道。但是诸多的不足又使得这部剧有了并不彻底的审美魅力。那么相较于《大明宫词》的进步意义,更为理想的存在便是《吕梁英雄传》这部电视剧。王伟国曾从“莎士比亚化”这一角度表达对于《吕梁英雄传》这部电视剧的肯定。它以正确的历史观和美学观,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生活与阶级民族矛盾。这部剧在敌我双方的战争冲突中表现了人物人性,展示了作为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导演以艺术化的途径,展现出真情实感与质朴表现。其中尤为感人的是剧中真实的空间形象,人物造型以及叙事氛围。导演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以象征与比喻、积累与对比、平行与交叉等丰富的艺术语言展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相较于“莎士比亚化”的与现实结合,对于“席勒式”的运用,要基于学术研究与正确认识。刘士林教授指出,对“席勒式”的学术研究至少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即:康德的哲学思辨、诗人的艺术感受与诗人哲学家的综合创造力。陈炎近年来所提倡的新国学研究,既是与席勒调和感性与理性相仿,更是新的整合与圆融的创造。新国学研究是以现代人立场,用现代人方法手段重新审视与解读传统文化,并用以指导现代人生活。这样的学术活动方式的选择,其伦理意义与席勒所坚守的学术似有相近之处。这样意志决断的选择,不同于当下浮躁的风气,不为做学术明星,不为获得学术名声,而只是为了学术本身,以超功利的爱的方式从事知识活动,这无疑是值得我们赞叹并为之努力的。
五、对“席勒式”的深度反思
由于“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这两者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经常使用于不同语境,其内涵与外延在国内外发展以及两者运用之间存在诸多不同,虽然有所关联,更多地是独立生成。因此对于“莎士比亚化”的深度思考在本文中且不多作论述。笔者曾好奇,席勒作为与歌德一同作为浪漫主义的提出者与先行者,为何在诸多评论中却是如此理性?浪漫主义所强调的表达自我的强烈倾向是如何能与理性并存的呢?显然,此处所言的席勒的理性,并非同我们一贯所认知的一样,代表了冷静,清醒与客观,而是指伦理与政治。其实,席勒与当时德国人所认知的理性相同,在当时政治自由难以得到保障的德国,席勒提出“让美走在自由之前”,认为现代社会人格已经分裂,只有追求理性才可达到人格圆满。在当时人们心理已然异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并不难理解席勒式的出现,人们需要精神上的统一号召,需要政治上的统一领导,更迫切地需要稳定的依靠,迫切需要获得和平与安宁。因此,席勒式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引导,成为时人的心灵依靠。其实古今中外,这样的依靠并不少见。在席勒逝世十几年后,乔治·奥维尔在《1984》中所表现的,亦是一种政治控制,不过较于席勒,讽刺意味占主导。且不论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手法,个人认为两者的政治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稍作比较。奥维尔书中的主人公温斯顿所处的大洋国有着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的强烈的政治控制,这样的控制已然变态,这样的国家满是历史的谎言。《1984》中所呈现的控制或许就是政治意味统一领导的极端,人们没有自由没有现实,席勒较之显然容易接受很多。同时代的中国,亦在经历着历史的重大转变——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建立之初,处于政治与时代的需要,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以书写政治意味较强的作品为主。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赵树理作为把现实与政治意味结合相当巧妙的作家,其作品因可读性,真实性与政治性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更获得政治主流的推崇。文学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认识性,倾向性以及其主导价值,文学创作中的创作动因与主体条件等等都决定了文学在历史与时代下,不可避免地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出当时当代人们的思想。它会为人们所接受,也会为人们所遗忘,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我们早已过了长征的时代,早已跨越饥饿贫苦的时代,再次回望过去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只能尽量将自己置于那个时代去体会,通过引起的共鸣去想象,而不能真正理解得彻底。同样,我们并未身处席勒同一时代,那么或许更应当跳出时代的束缚,从现代意味上来理解。当然,席勒式是一种具有修饰性的概念,并非完全针对席勒个人而言。“莎士比亚化”因其现实性,表现人性与生活的复杂而为马克思所提倡,莎翁也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为杰出的戏剧家与诗人而广为人知。然,席勒或许是有“席勒式”的阴影而颇受影响,抑或是其个人原因为主导,其知名度且不用言莎翁,哪怕与同时代的挚友歌德相比都相差甚许。马克思本身提出“席勒式”这一观念,既是点出席勒在创作戏剧中的不足,更是对拉萨尔将这种缺点进行恶性发展的批评。这或许在启示我们,先辈提炼出理论的高度固然不易,但我们或许更要从多方面客观地考虑作家。这不仅是缘于作家本身各有所长,而且缘于时代对于作家的影响,影响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对于他们的态度与评价。那么我们既然已经错过了那个时代,不如以我们新时代的观点,包容地看待,而不是一味地依循前人却毫无思考。
六、“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创新阐释与现实指导意义
自瞿秋白将“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介绍到中国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的探讨与研究在中国已经经历了近百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简单地将“莎士比亚化”等同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显然是存疑的。笔者认为,“莎士比亚化”并不必直接地归为现实主义,而是可以使涵义包容更多,即为与“席勒式”相对的更结合现实、更贴近生活的创作范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某一主义或某一观念。傅其三教授在评价曾簇林《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纲要》》一书时,对曾簇林从艺术本体的角度科学阐释“莎士比亚化”这一美学总命题的内涵的方式大为赞赏,因其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所讲到的“莎士比亚化”的美学总命题对“莎士比亚化”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未进行明确的界定,而是以“莎士比亚化”的艺术生产贯穿于立论之中,这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李伟民教授曾从对立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两种学说在中国不同时期与政治环境下的不同理解,并且比较中国莎学研究体系相较于西方的多元莎学研究间的异同,以此来构成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立脚点的莎学研究。那么现如今,对于“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理解与研究必定要从新的维度进行诠释,才能使这一理论继续散发活力。我们也可以追根溯源,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老师黑格尔及黑格尔美学的观点来阐释。李跃红教授对于这一文论的全新阐释便是取自于黑格尔美学。两者的概念都是来源于黑格尔美学,更与黑格尔美学密不可分,而“莎士比亚化”这一概念蕴含着黑格尔的美学精华。因此,从黑格尔美学的角度可以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新的诠释空间的挖掘,进而说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论诠释的新的原则。李教授通过“席勒式”从对立面界定“莎士比亚化”的内涵,即艺术为之艺术的普遍性的特征,更从新的维度阐述了“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的关系,即并未把“莎士比亚化”直接地就等同于现实主义,而是阐释为与“席勒式”的抽象主义相对的全部真正艺术。这样的创新阐释,无疑使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文艺观念未来在中国更好地发展。正如冯宪光教授所言,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要接地气,要以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认真的态度来对中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进行研究,才能建设创新性理论以此推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
七、结语
随着各国政治形势与文艺政策的调整与改变,“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两个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更有着相当的学者与创作者对其发扬与提倡。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的文艺理论体系都在一步步完善,在各个方面都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国作为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学积淀的大国,当进一步对这两者进行客观与深入的研究,积极创新。而于我们这些后辈,当站在时代的角度,以过去为基础来了解,以现在为根本来发现,在岁月的更迭中不断思考与探索,更好地理解与继承先辈留下的精神财富,以此繁荣中国文艺事业,使其拥有源源不断的生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