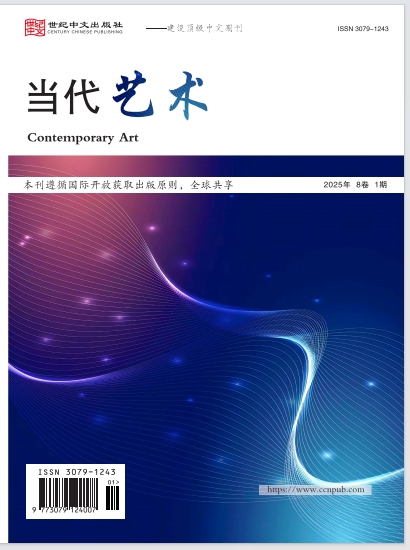羌族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能歌善舞的民族之一,歌舞艺术在羌族数千年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伴随着羌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用更加的突出。羌族舞蹈表现出古朴而又典雅、热情而又奔放、粗犷而又细腻、豪放而又优美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数千年时间长河中羌族民间舞蹈随着社会生产和发展变得更加具有艺术魅力,因此对其和艺术特征和发展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对我国舞蹈文化研究、民族文化传承有着特殊意义。
一、羌族舞蹈的特点
羌族生活在四川岷江流域,是我国古老民族的其中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羌族舞蹈在民风习俗和群众生活中有重要的意义,每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种植、收割、放牧、狩猎、盖房、治病等活动,羌族人民都要跳舞。从流传至今的羌族舞蹈艺术中,还反映出羌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汉族、藏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传统的渊源关系。羌族民间舞蹈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以巫表演为主的祭祀舞——巫舞和“锅庄”(羌语称锅庄为“洒朗”)。
羌族舞蹈最早出现于祭祀活动,是祭祀舞蹈的一种。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事物和物质运动规律认识不全,认为世间万物是由一种超能力支配的现象,于是逐渐诞生了神鬼的概念。在此情况下,人们如果生病或者发生不好的现象,便会请巫师进行祭祀,在祭祀活动中逐渐形成特有的舞蹈种类,认为利用舞蹈能够与神鬼交流,实现是人们的愿望,此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出庄重、灵活、单线条活动为主。
二、羌族舞蹈的艺术特征
1、歌舞合一的和谐美
“羌族民间艺术中,歌舞是一个结合的整体,有歌才有舞,有舞就有歌。”羌族的传统民间舞蹈,除“布兹拉”有单面羊皮鼓和响盘做道具,并为舞蹈伴奏外,其他舞种都没有乐器伴奏,舞蹈或以呼喊、踏地声为节奏,或和以古羌语吟唱的古老民间歌曲踏歌曼舞,形式古拙,风格质朴。古歌或欢快热烈、或沉稳凝重、或粗犷奔放,节奏自由,山歌风味浓郁,交替反复,感情质朴;歌词的内容多表示欢迎、祈福、丰收、祭祀和怀念等内容。
2、围火连袂的古朴美
羌族人民围火而舞的习俗由来已久,羌族民间故事《燃比娃取火》中说,远古的时候,羌族青年燃比娃(天神格蒙西与羌族姑娘阿勿巴吉之子)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从他阿爸那里取回火种(两块白石),并按照阿爸的旨意,用白石相撞发出火星,点燃干草和树枝,燃起了羌家第一堆篝火。人们围着这象征温暖、幸福的火堆,欢乐地唱啊、跳啊……[1]从此每逢丰收节庆、婚丧嫁娶、消灾祈福、祭祀鬼神,羌族人民都要点起“万年火”,围着熊熊烈火,跳起不同形式的传统舞蹈。“萨朗”一般是男队在前,女队在后,相互拉手,形成圆圈,围着篝火逆时针方向行进,欢歌劲舞。在圆圈的行进中,在火光的照耀下歌舞不断反复,速度由慢渐快,情绪逐渐热烈。“哟粗布”多在室内进行,参加人数不限,男女两队拉手连袂呈弧形面向火塘站立,舞蹈时也多沿逆时针方向起舞,时而一唱一和,时而左右移动,时而拉手连臂,时而甩手搭肩,往往通宵达旦,尽兴方散。“天地可以交合,阴阳可以协调,心心可以相应”[2],这种祖辈们流传下来的最原始古朴的面对着面,手牵着手,围着火堆共向一个圆心,伴随着整齐统一的节奏踏歌起舞的形式,是千百年来羌人在与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坚毅、团结、乐观的精神表达。其质朴的生存愿望直接影响了羌人的审美心理,从而塑造了羌族舞蹈围火连袂的古朴美。
3、神秘虔诚的虚幻美
羌族地区每当举行各种祭祀或习俗活动,无不以舞蹈贯穿始终,无论祭神还愿、祈福消灾、除病祛魔,还是老人丧葬、送魂归天、驱鬼辟邪。“释比”头戴金丝猴皮帽,肩扛神棍,手执响盘(铜制盘铃)率众舞者,击鼓而舞,跳起传统的“布兹拉”,他们打着皮鼓不断变换队形,来回跳跃、左右穿梭,鼓声震天,气势雄壮;“哟粗布”中除了模拟生产劳作以外,也明显含有祭祀活动中的动作和虔诚的心理气质,有老羌人说:“我们的哟粗布就是怀着赤诚的心,向天神祈祷的意思”;就是“萨朗”和“巴绒”也是源于对“萨朗姐”(歌舞女神)的纪念。无论是祭神还是娱神,都是源于羌族人民将生活的美好愿望寄予“神”的精神诉求,当这一诉求直接作用于这些舞蹈表现形式时,所带来的是无比神秘、无比虔诚的虚幻美,所产生的视听感受是直击心灵、令人震撼的。
三、羌族舞蹈的发展
1、运用“虚像”
对羌舞进行革新,使它更加完善,是促进羌舞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种艺术要想常给人们新鲜感,使人隋绪兴奋,非如此不可,羌舞也不例外。羌舞的各个舞种或欢快跳跃,或沉稳滞重,或粗犷虔诚,或稳重端庄,但身体轴向转动这一基本要素,却贯穿在各个舞种之中,成为它们的基本韵律。
我们既要传承羌舞的传统风格与特点,如围着篝火起舞的形式,如“萨朗”原始的踏、悠、摆、转等舞蹈动作,又要顺应时代与观众的需要,对这一古老而有生命力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积极探索和开拓,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形式转化和艺术升华。
2、挖掘形的广度和深度
人的形体动作是舞蹈的主要表现手段,但并不是人的各种形体动作都能成为舞蹈,只有那些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内容的动作,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和美化之后,形成一种有节奏、有规律的运动形态,才能被称作舞蹈。
羌舞的突出特点是连臂踏舞和躯体轴向转动,这是经过羌族人民多年实践的结果。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羌舞在创作上因循守旧,不敢逾越,使得旧有形式渐渐成为束缚羌舞发展的枷锁。舞蹈肢体语言如果缺乏创新,则会导致形体动作僵化,表现力也必然会大大削弱。因此,羌舞应该标新立异,大胆提炼羌族人民现代生活中的肢体语言素材并加以艺术化,在挖掘形的广度、深度上下功夫。
四、结束语
羌舞作为羌民族独有的一种舞蹈,尽管目前处于由盛转衰的严峻态势,但它不会走向消亡。羌舞的传承与发展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保留原生态羌舞,采用摄影、摄像、文字记载等方式,进行分类归档,为人们提供研究和创作的参照。二是拓展羌舞的表现内容和应用范围。如同汉民族的秧歌一样,把历史传说或现实生活融入其内,或是将羌舞的形式要素运用于现代舞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羌舞这一民族民间的自娱形式能在更专业的舞台、更广阔的空间去散发它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肖丽娟.羌族舞蹈的艺术特征与发展对策新探[J].四川戏剧,2020.
[2]范燕华,龙有成.文化产业发展视域下的羌族舞蹈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01):104-108.
[3]张锦江.羌族舞蹈的原生态形式到舞台形式的流变与呈现[D].西北民族大学,2019.
[4]唐必,耀赵,容芳.论汉中地区羌族舞蹈的集会与自娱性特点——以汉中羌族锅庄舞为例[J].黄河之声,2017,479(02):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