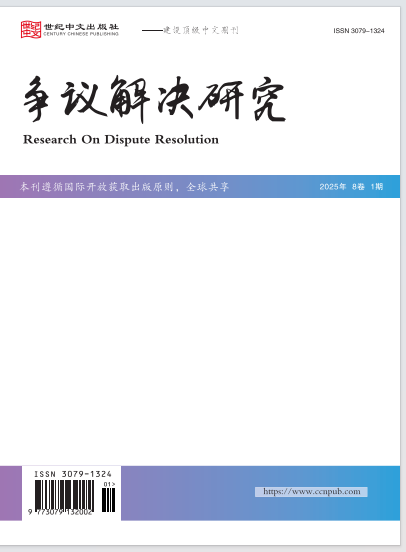在国际社会无论是卢旺达刑庭、前南国际刑庭,还是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均需在实践中展开刑事司法活动,国际刑法得以不断发展,这对国际视域中司法问题的高效解决有益,其中共同犯罪理论构建及司法认定属于必须解决的问题,共犯、正犯的区分则为重中之重。国内外刑事案件存在事实特性方面的差异,国际刑事案件相对复杂,主要源于犯罪主体多,其行为关系较难梳理,这使得共犯问题很难判定,加之牵涉刑事案件的各国法律文化不尽相同,经常会出现拉锯性博弈现象,这无疑加剧了共犯犯罪行为判定的难度。基于此,为使国际刑法中的团伙共同犯罪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分析国际刑法中的行为控制理论显得尤为重要。
1 团伙共同犯罪理论概述
团伙犯罪有着相同的目标,共同目的理论源于英美刑法实践经验的总结,通常正犯在团伙犯罪中起着主导作用,可直接导致犯罪事实的发生,在共同犯罪条件下团伙中的每个人有着相同犯罪目的,并不能精准判定直接犯罪行为实施者是哪一个。依据固有英美刑法理论不能对共犯团伙每位成员实施处罚。为弥补犯罪处罚领域的疏漏之处提出了团伙共同犯罪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团伙共同犯罪理论指出,只要成员犯罪目的相同那么团伙犯罪事实客观存在,则可认定每位成员均为共犯,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国际刑法理论在未启用行为控制理论以前司法实践领域中团伙共犯理论影响较大,在判决中主要规定有以下几个:一是有共同犯罪的目的或计划;二是一伙行为人;三是被起诉者在共同计划中有着参与行为且无需直接参与特定犯罪,只要影响或辅助便能完成共同计划。团伙共同犯罪理论包括扩展模式、系统模式、基础模式三中类型,上述类型对共同计划中犯罪行为有着不同的判定,这使得团伙共同犯罪理论涉及范围更广。其中,扩展模式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共同计划之外,尽管如此对共同计划的实施可带来具有预见性的影响;系统模式是指共同犯罪团伙身处囚禁系统,行政单位、军队及其他组织实施某种犯罪;基础模式是指几个人计划实施犯罪,每个行为人均执行相同计划,参与者犯罪意图一致,每个人均需对犯罪行为负责。通过对团伙共犯理论进行总结可知,团伙共同犯罪计划或目的相同,正犯在实质性犯罪活动中的影响要求有所降低,行为类型细分且对其加以定义,正犯认定理论及范围有所拓展,这使得相关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得以优化[1]。
2 行为控制理论及其评价
2.1 主客观偏废、主客观并存
在德国早期司法审判中主观理论是正犯认定的主要依据,从“意志”层面对共犯、正犯的身份加以判定,“意志”划分理论有两个,一是恶意理论,二是利益理论,前者指出正犯独立意志较强,共犯意志相对不独立,后者指出期望获取利益是正犯意志形成的动因,共犯则无利益追求。客观理论在发展中逐渐用实质客观说代替形式客观说,后者认为正犯符合刑法分则的描述,在团伙中的其他人则属于帮助犯及教唆犯,这种认定方式有碍共同正犯与间接正犯的认定,实质客观说则在身心因果影响理论、行为人监督理论、行为前及行为时参与理论、因果贡献必然联系等理论对犯罪行为加以判定,然而综合理论联合应用难度较大。在主客观偏废后行为控制理论开始强调主客观并存,基于行为控制理论对功能性控制、意志控制等概念加以界定,在犯罪中影响力较大的核心或关键人物属于正犯,为消除极端分歧对理论加以细分,从亲手犯罪、义务犯罪及控制犯罪角度出发对犯罪行为进行综合性判定。
2.2 事实性、规范性交融
正犯认定理论经过因果性及事实性认定逐步发展为具有规范性的认定理论,在主客观并存的基础上还可联合其他理论增强定罪考量的机能性与规范性,这使得正犯认定可打破固有局限,凸显行为认定的实质合理性。在规范性判定与事实性判定交融的进程中理论存在不稳定的问题,犯罪控制概念较为模糊,根据控制犯罪原则亦不能简单推论犯罪行为,作为指导性观点相关理论对共犯的界定有待具体深入。
2.3 行为控制理论引入
基于行为控制理论的共同正犯构成包含主客观要素,其中客观要素有共同计划、正犯行为人、协议(默认)、共同实施、共同控制犯罪行为,主观要素有共同认识到有实质性犯罪发生的可能、主观上有特殊犯罪要求。间接正犯理论主要活跃于国际刑法舞台,在事实认定中有着主客观结合、规范性与事实性结合的特点,围绕“组织控制”这种控制形式不断扩充正犯认定理论,存在理论自洽危机,亦有过度强调实质性的倾向。行为控制理论对理性划分刑罚权边界来讲影响较大,为正犯在国际刑法中的认定提供依据,同时需解决理论实质化严重的问题[2]。
3 行为控制理论批判发展
3.1 从事实层面着手批判发展
从事实层面来讲国际刑法案件、国内刑法案件差别较大,前者具有犯罪关系复杂、犯罪主体多且有层级性等特点,因为确切认定直接犯罪实施者的难度较大,所以实际操控人员很难追责,形式化共犯理论无法厘清复杂的国际犯罪关系,这就需要应用组织控制理论、团伙共犯理论,然而过度强调实质性的理论有碍法治原则的运用,需法治原则在共犯关系的考量上寻求平衡,增强基于国际刑法的行为控制剖析实效性。
3.2 从规范层面着手批判发展
国内刑法、国际刑法差异较大,后者覆盖范围更广,仅从教义学方法角度出发予以阐述显然会使共犯理论研究视野变窄。国际刑法涉及理论复杂,需着眼于法律全球化,不能仅关注概念与学说,应通过实践并在实用主义加持下助推行为控制理论向着凝聚性、逻辑性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中重塑理论,使行为控制理论能既规范又高效,可在国际刑法中起到重要作用。
3.1 从适宜层面着手批判发展
源于德国的行为控制理论在国际刑法中的有效应用可解决团伙共犯行为认定相关难题,在刑事政策及罪刑法制约与促进关系的共同作用下正犯认定理论不断发展,可增强理论的规范性与适宜性。在行为控制理论活跃于国际刑法应用领域的基础上调节刑事政策、罪刑法二者关系,为组织控制等学说理论的应用指明着力点,还需在冲突与融合中增强法系的协调性,确保行为控制理论能在现阶段的国际刑法中有一席之地。虽然学说理论较为复杂,法系之间融合难度客观存在,但以法律渊源为依托构建共犯基本理论属于基础性条件,不能生搬套用行为控制理论,要关注共犯问题在法系中的差异,还需在国际刑法中凸显行为控制理论的适宜性,这离不开司法实践经验的累积与总结,尤其要在新型国际犯罪审判中寻求共识,继而推动行为控制理论不断发展[3]。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际刑法中的行为控制理论是认定正犯的重要依据,可科学划定犯罪行为逻辑判断边界,与团伙共犯理论相比其说理性及实效性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在复杂的国际刑法案件中,行为控制理论对共犯形态的判定难度较大,意图在理论扩张的前提下应对正犯判定复杂化挑战,增强理论的自洽性,健全共犯立法结构并提出国际刑法审判方案。基于此,为使国际刑法层面的行为控制理论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需从事实层面、规范层面及适宜层面切入助法律体系交融,在制约与促进的关系中达成共识,继而提升国家刑法中行为控制理论的应用水平。
参考文献:
[1] 江溯. 国际刑法中的行为控制理论[J]. 2021(2015-2):176-192.
[2] 杨诗韵. 国家不能成为国际刑法的主体[J]. 2021(2013-2):27-29.
[3] 刘继云, 孙绍荣. 行为控制理论研究综述[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 26(005):206-207.
作者简介:魏毓航(1994,2-),女,汉族,本科,四级警长,研究方向:刑法。